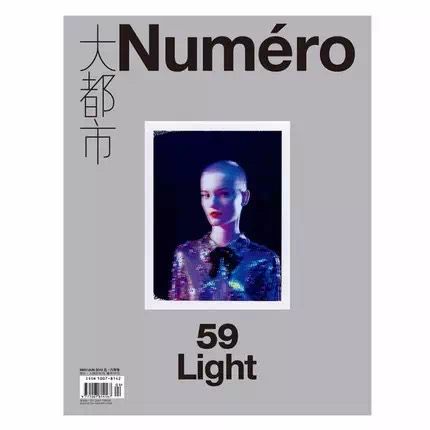我不追求时髦,我追求简朴的未来主义、乌托邦或者反乌托邦。
马海平(MHP)多年来都是上海Techno圈无法略过的代表人物。学美术出身的他这些年在上海当DJ,在国外知名Techno厂牌发作品,和戏剧界、艺术界的朋友一 起玩跨界实验噪音,办电台推广电子乐,在复旦大学教授现代音乐史,在上海戏剧学院研学当代艺术,分身于MHP、V/O/ I/D、上海异人唱馆、友军电台……今年4月,全新专辑《折叠痕迹》发行,“上海Techno之子”再次树立上海Techno新标杆。
2012年马海平通过美国底特律厂牌Cratesavers International发行了自己的黑胶唱片《四方来朝》,使他成为第一个在Techno音乐发源地发行唱片的中国电子音乐人,《折叠痕迹》是马海平第一次在国内厂牌发行的电子概念专辑,整张专辑汇集他最近几年电子音乐创作精华,老歌占1/3,包括《黄昏之光》(2015,EP)和《四方来朝》(2012,EP),整张专辑融入他对光影、音乐、未来主义、科幻等主题的喜爱。
“我希望整张专辑都充满画面感。有些潮湿,有些阳光,丰富细腻。”学绘画科班的马老师说:“创作《黄昏之光》时,整个画面感是一种橙色——城市黄昏,有一些云,太阳光从云后洒下来的画面感。专辑里我没有放适合舞池的重型Techno,一方面考虑中国观众不一定会特别喜欢,另一方面想保持专辑的流畅性,让它更细腻精美,色彩感更强,更旋律化。”
Numéro:新专辑为什么叫《折叠痕迹》?
马海平:“折叠”有三层意思。第一,未来主义绘画的“折叠”。唱片封面就有未来主义绘画特征。电子音乐有未来主义倾向,我做的是未来主义音乐,我要从根上去寻找。我唱片里有一首歌叫《未来主义宣言》,是 1909年《未来主义宣言》节选。第二,光的折叠。色彩感是我想要的。唱片里有很多和光有关的东西,唱片封面的细腻度有光的感觉,歌的名字也和光有关。比如最后一首歌叫《墨尔本的阳光》,上海的雾霾现在已经习惯了,但你到墨尔本去能感到透明度是不一样的。我录了很多这样的东西。第三是《银翼杀手》(Blade Runner,1982)结尾的独角兽折纸。我特别喜欢这部电影。“痕迹”指音乐是时间性的、 流逝的。
Numéro:新专辑除了提到墨尔本还涉及哪些城市?
马海平:主要是上海。我这张唱片想做概念唱片。我想尽量从文学性、 故事性去挖“情节性”,比如有一首歌《梅雨之城》说上海的雨季黄梅天,黄梅天的下午你会看到有时候天是橙色,甚至紫色的。从延安路高架开上去,从重庆路到外滩那段,你可以看到房子越来越高,到最后是一条河,对面是浦东。这个场景很漂亮。城市可以成为音乐的主题,比如底特律和芝加哥,我觉得上海也可以。
Numéro:新专辑里有古筝?
马海平:最后一首《墨尔本的阳光》找了王萌,一位和我玩得蛮久的弹古筝的歌手。她之前给Gorillaz弹过古筝。我和她去年12月份一起去墨尔本录了很多采样,有些是拿iPhone录的,有些是采样机录的,我弹比较简单的合成器,她弹一些即兴,我把这些放在了最后一首。
Numéro:这张专辑蛮适合在办公室放。
马海平:是的。我有一种推广音乐的责任感。走五步会死,可能走三步就可以活。要让观众接受这样的音乐,你不能走得太前面。或者说旋律要比较到位,因为中国观众是要一些旋律的。假如一首五分钟的歌从头到尾一样,就一个Loop(循环),中国人就不要听。电子舞曲最难的不是做一首曲子,而是做一个四小节的Loop,因为Loop出来这首歌也出来了,这就是说,在Club里跟着鼓跳舞,如果鼓和贝斯重复四小节能让你跳起来,重复20遍还是让你跳起来。

Numéro:四小节是一个魔咒?
马海平:这个概念不是来自于现在的DJ或者制作人。埃里克·萨帝(Éric Alfred Leslie Satie)的《梨形曲》就是一个循环,他最早提出这个概念。1960年代有人做极简主义(Minimal),那些是钢琴曲,比如像菲利普·格拉斯(Philip Glass)。他和马友友合作过纪录片《战争生活》(Naqoyqatsi,2002),里面始终在拉大提琴,16小节稍微加一个音,再加一个音,就特别像电子音乐。Kraftwerk就是学了这些学院派的东西,变成音乐不要大段也可以奏效。这是一个很当代的观念,再后来就变成电子舞曲。所以我说实验音乐家实验的东西,就像你生产一种药,你在实验室里实验,到最后是要有用的。
Numéro:学美术半路出家做音乐的人和专业学音乐的人相比,在创作音乐的时候有哪些区别?
马海平:我认识很多上海音乐学院的朋友,我们的东西会给他们启发。比如画面感、对音色的理解,他们做电子音乐基本上不研究合成器,不考虑音色,还是五线谱写好,然后来弹,当纯乐器来做,但呈现出来的也是电子。他们更偏向传统作曲,我们考虑概念专辑、音色、文学性、画面性。
Numéro:听说毕业多年后,最近你又重返上海戏剧学院读书?
马海平:最近在上海戏剧学院读当代艺术在职研究生(MFA),上戏是一个很好的平台,会给研究生和老师提供项目基金做项目,可以拿更多的钱做音乐以外的东西。我特别想做剧场,以音乐为主题,融合演出、影像、肢体表演。我不想把自己局限在音乐里,想有更多可能性,但剧场没有资金支持很难做。我想把以前的资源整合起来——老师、朋友,包括像在独立戏剧界特别有名的学妹蔡艺芸,去年我们曾经一起在杭州做过剧场作品《写诗》,我即兴现场配乐,今年6月我会替她的先锋版实景话剧《雷雨》做配乐。

Numéro:你会去做电影配乐吗?
马海平:有机会肯定会尝试。我本身学戏剧,之前也做过配乐,我给艺术家杨泳梁的作品做原声,2012年出了配套原声碟《极夜之昼》。对于小众电影而言,电子音乐人的可能性很多,曾经的很多独立音乐人现在都在做电影配乐,这是好事。做音乐就两个东西挣钱,电影配乐和流行音乐。我去年演出很多,而且在外滩美术馆、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、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等多个现当代美术馆。在美术馆的演出是做实验即兴,不是舞曲。有古筝、低音单簧管、大号,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馆庆还请了低音贝斯和小提琴手。我们在现场用音乐对话,比如小提琴先出来,大号怎么去呼应,古筝怎么去呼应。其实十几年前做舞曲之前我就是玩这样的音乐,那时候有个乐队叫Junkyard,玩吉他噪音即兴和日本实验摇滚。这些年我回头又来做实验是因为当时没有特别好的乐手,而现在的乐手还可以。乐手很重要,比如我的低音单簧管乐手今年69岁,在1970年代的时候就和德国激浪派大师Peter Brötzmann合作了。
Numéro:介绍一下你的电台节目友军电台。做电台的初衷是什么?
马海平:友军电台节目分为2块,一块偏电子舞曲,主要选制作人和DJ。还有一块友军试验田,学院派的和民间搞噪音实验、声音艺术的。我找那些大家不是特别知道的,还有身边真的认真在做音乐但名气没打开的。2015年初开始做,可以在荔枝FM、喜马拉雅APP收听到。像我们从1990年代开始听电子音乐的人,一开始就觉得电子音乐是实验音乐,是噪音。后来才接触到舞曲。通过这个电台给大家一个宽泛的概念,电子音乐既包括Club音乐,又包括实验音乐。我希望通过电台介绍不同种类的音乐人,让大家了解电子音乐是很大一个观念。另外本土电子音乐其实很丰富,但大家还是只知道其中一部分。我希望本土也能像国外一样,逐渐形成体系、脉络。大家各玩各的,但每个点都已经布好局,可能过一段时间就会成长起来,会越来越丰富,就像西方音乐。
Numéro:为什么叫友军电台?
马海平:有人问我你是和敌台做对吗?那不是的。像Underground Resistance翻译过来叫地下反抗组织。友军也有这样一层意思。我们很友好,有一种类似于黑人的帮派精神,能一起做一些事情。
Numéro:去年你为中国科幻银河奖主题歌作词,纪敏佳演唱,刘慈欣作序。是什么促成了这次合作?
马海平:《科幻世界》副主编杨枫找的我,说银河奖不是很活泼,你搞电子音乐嘛,和科幻也有关系,那就做一个吧。我特别喜欢《科幻世界》这帮人。2010年这帮人联合起来把主编李昶弹劾了,搞得特别大。科幻里面有很多反抗的东西,这帮人看上去斯斯文文“书呆子”,其实内心特别能抵抗,很反叛。刘慈欣也是。我见过他一次,说话斯文,但他的文章里对世界的理解非常具有反叛性。
Numéro:所以你一直是科幻文学爱好者?
马海平:我特别喜欢科幻,尤其黄金时代的,克拉克(Sir Arthur Charles Clarke)、阿西莫夫(Isaac Asimov)、海因莱因(Robert A.Heinlein)、菲利浦·狄克(Philip K. Dick)、弗诺·文奇(Vernor SteffenVinge )。华裔的刘宇昆、特德·蒋(姜峯楠,Ted Chiang)。这些和我的音乐都有关。我不追求时髦,我追求简朴的未来主义、乌托邦或者反乌托邦。
撰文 九间 / 编辑 刘星 Cheyne Liu / 摄影 海螺壳
刊于《Numéro大都市》,点击这里去官网查看